日前,著名台灣民俗學者蔡亦竹先生新書出版,更在最近撰寫了一篇文章,談論了本能寺之變發生原因的分析文章,引用及介紹了不少著名日本小說家、漫畫家的觀點,多角度分析了這場十分出名的歷史事件。
筆者有幸也在一年前出版了相關的作品,版友人問及對蔡教授專文的看法,在此以討論交流的觀點,從史學角度談談自己的看法。有興趣的朋友,歡迎互相比對。
注:以下由於篇幅關係,筆者在下面集中就蔡教授的個人觀點,談自己的想法,「」部分為教授原文的相關內容。
首先,蔡教授就事變的其一個當事人—織田信長作評價:
「戰國時代的改革者信長貫徹「樂市樂座」、也就是經濟自由化的偉大改革,所以必須和盤據於日本、尤其是近畿時代的各種宗教及舊秩序勢力作對到底。而在信長之前稀鬆平常的宗教戰爭,也因為織田家對一向一揆等宗教勢力幾近暴虐的強力鎮壓而消失於日本」
首先站在史學的角度而言,「一向一揆」既是不合乎史實的概念,同時將信長與本願寺的戰爭定性為宗教與世俗的戰爭是不太正確的,因為信長從來沒以殲滅本願寺為前提,對本願寺發動戰爭,起初是本願寺,還有之前的比叡山延曆寺都因為選擇跟六角、淺井、三好等勢力聯手,拒絕向新到京都的信長合作而引起戰爭,本願寺更是突襲織田信長跟將軍足利義昭,這裡的問題是比叡山跟本願寺都跟反信長勢力有長期的合作關係,自然不會輕易賣信長的帳了,這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宗教戰爭,而是一場混合政治俗權的事件。
再說,想必蔡教授也知道,江戶以前的日本社會宗教佔據生活及政治的比重比江戶時代大很多,難以輕易切割,同時也難以單方面理解。
「就因為信長對帶著暴力裝置的宗教團體進行鐵槌制裁,才讓日本成為世界中少見的宗教戰爭免疫國之一。」
「鐵槌制裁」與否是一個定義的問題,的確攻擊比叡山跟與本願寺的長期對抗是暴力、血腥的。拙著第二冊也提到信長在長島、越前進行殲滅戰,以阻止盤據當地,響應本願寺的教徒對織田家的統治構成威脅。說實在,拙著第一冊已提到,本願寺還有法華宗等教派在戰國時代因為政治問題被鎮壓、被攻擊絕不始於信長,禁止本願寺為首的淨土真宗傳教的大名比比皆是,信長與本願寺的戰爭之所以被放大來談,既因為織田家當時的勢力最大,而本願寺為了戰勝信長,也動員手下群眾在各地起事,反過來說,信長暴戾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之外,何不反過來想想為什麼本願寺可以跟信長周旋良久?只能單一「英雄」、「權力者」的角度去理解,是不能很好地明白戰國日本人的,這也是拙著最想強調和著力最大的一個主張。
「荒木村重的背叛對於當時的織田家有多大的衝擊,只要看過大河連續劇「軍師官兵衛」的朋友就可以體會。而且荒木背叛之後其實織田家還送了使者請他回心轉意而且還一送就是兩次,被荒木關成跛腳的黑田官兵衛就是第二次的使者。結果荒木全家會被殺,也是因為信長提出「只要交出城池就放過你不然殺你全家」的要求被荒木打槍造成的結果。而且他老兄本人最後還逃之夭夭,過程中更連累了隱匿荒木一黨的高野山僧侶數百人被殺。」
事實上荒木村重逃出後仍然廣發書信,要本願寺、毛利各家盡快出兵,可惜不久之後原本尚算積極的本願寺被信長、秀吉連場殲滅戰嚇壞,加上毛利家也無法打敗秀吉,於是本願寺開始摸索與信長議和的機會,村重最終空負「逃之夭夭」的罵名至今。
當然這不代表殺戮代表正義。但是信長的這些激烈舉動,正好顯示出與舊秩序對幹的信長遭遇到的是多麼強大的抵抗。
「信長雖然不像遊戲或是漫畫描寫裏的那麼完全破舊立新,包括早期的利用足利將軍權威和後期的搬請天皇出來與本願寺間調停衝突,其實都看得出信長沿革舊秩序倫理的一面。」
既然蔡教授認同信長並不完全排斥舊有傳統及制度(當然,因為這是事實),那為還要說信長「與舊秩序對幹」,「對於宗教的殘忍鎮壓」,更云信長「遭遇到的是多麼強大的抵抗」呢?所謂的「舊秩序」如是指他跟本願寺、比叡山等傳統佛教勢力的對抗的話,那如前所述,這是不盡然的理解。如果信長要「與舊秩序對幹」,為什麼要接受與本願寺、比叡山和解?反過來說,作出「多麼強大的抵抗」的傳統勢力如是因為信長「拳頭大」而願意妥協,那麼這不也解釋了他們向信長發動的抗爭是政治問題大於宗教問題,本質上也不是新舊秩序的對抗,因為這些勢力只是跟信長和解,不對抗而已,而不是無條件投降,兩者差異之大,無需多解釋。
「對於商業的重視和兵農分離等政策,不但劃時代而且完全被他的後繼者豐臣秀吉完全繼承。」
其實戰國大名都十分重視商業,不獨信長一人,而所謂的「樂市樂座」的確不是所有戰國大名都有做,但也非信長首創獨設,「劃時代」與否實在見仁見智。要說明樂市樂座的問題值得寫一篇長文,在這裡簡單去說的話,信長的樂市樂座政策只在很局部的地區實行,而且是當地商戶提出,再要求信長下令批准的,同時信長也沒有將壟斷專賣的「座」完全廢除,反而部分還得到信長保護。
至於秀吉的政策在廢除「座」等特權上比信長更徹底,但應否將之理解為沿襲信長政策,則有很大的疑問及爭論,數十年前的日本史學界為了有系統地理解信長到秀吉,再到家康的統一天下進程,刻意讓他們「一脈相承」,即「信長影響秀吉,秀吉影響家康」,即使部分可取,但事實上卻有點過分簡單化的問題。
「但是真正讓信長死於非命的原因,應該是他的權力觀⋯⋯光秀要抗「暴」的絕不是上述的那些所謂罪狀,更不是大屠殺或是燒比叡山不然光秀早在多年前就該下手了。司馬指出驅使光秀行動的,就是日本人潛藏於心底的對於「獨裁」的恐懼。」
「信長從統一尾張這個小地方、又打敗了當時有力大名今川義元之後,就完全確立了他在織田家中的絕對地位。再加上織田家本來就是個小大名,所以當然歷史、人事包袱就少。所以這種類似暴發戶的背景,才讓他會犯早期自稱「上總守」的笑話。」
這是一個誤會,第一是織田家族在戰國時代(也就是室町時代)時已有一定的名聲,遠至室町將軍也有交流。當然,看蔡教授的內容,相信說的織田家應是指信長出身的「織田彈正忠家」,即各個織田家中的一個分支,但是即使如此,織田彈正忠家在當時即使在地位上不能跟名門今川家相比,但我竊以為也不能以「小大名」來理解,因為在信長父親時,已是一個急速冒升的新興勢力,與當時的文化界、學術界人士都廣有交流,軟實力不足,又與今川家、齋藤家爭輝奪艷。(有關織田家的崛起,詳見拙作《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中冊)
另外,關於「自稱「上總守」的笑話」,老實說筆者不知教授指所謂的「笑話」是指什麼。如果是指信長自取了一個跟自己出生地無關的「上總介」官名的話,這也不算什麼笑話,因為這樣的事情在當時很普遍。如今川義元之子今川氏真也稱「上總介」,西國的老英雄毛利元就的官名是「陸奧守」,伊達政宗一開始的官位是「美作守」,這些官名亂套的原因就是因為形式比實際重要,除了特定官位(高級的)有特殊意義外,國守(當時稱為「受領」)在當時大部分都是自由「使用」,真的假的「xx守」同時存在,所以竊以為這既然並非信長一人為之,那麼恐怕也跟「暴發戶」無關,更加跟信長是否用人唯才無關。
事實上,除了信長外,不少戰國大名也任用來歷不明、出身不高的人材為重臣,著名的上杉謙信的重臣河田長親、豐臣秀吉的忠臣石田三成,伊達政宗的左右手片倉景綱都是這樣的例子。固然,這兩人在結果上所獲得的發揮空間與蔡教授提到的秀吉、瀧川一益的情況相比有差,誰高誰低也難以比較,總之筆者只認為,不只信長唯才是用,信長以外的大名也絕非只看老爸是誰才用的。
那麼,信長急速成霸的原因是什麼呢?信長的才幹自是不容否認的,但這跟信長用低下階層出身的人為重臣又有沒有必然關係呢?這是一個有趣的課題,然而「織田家永遠充滿效率和決斷力,也讓織田家得以快速膨脹」的問題,筆者在日前的信長講座中說道,信長很多時,尤其是軍事決策上,行事是獨斷專行的,決定了才告知他人,所以很多家臣會無所適從,但不代表信長所有事都是沒有商量,沒有餘地,破壞教授所謂的「和」,同時地信長的家臣既敬畏信長,也會有時出言頂撞,那位被信長放逐的老臣佐久間信盛就是因此被信長記恨了,證明信長既是偏向獨裁,但卻不是讓群臣低頭,唯唯諾諾的絕對君主。
那麼,是否如蔡教授說,因為信長「無視其他人意志的決策方式」,不「符合「和」的精神」才被光秀暗殺呢?筆者認為光秀在事變前已跟隨信長十年有餘,信長行事方式不妥,受不了的話,理應早早離去,或者像荒木村重一樣早早叛變,但又為什麼「忍」了十多年才受不了呢?這又好像有點難說的過去,如是者,也難說明為什麼重臣之中,只有光秀一人謀反,難道說其他重臣,如柴田勝家、豐臣秀吉都都無意「以和為貴」嗎?
最後,關於光秀是不是「作為一個日本人的「深層心意」終於讓他爆發而發動叛變」,因為信長「這種違反「以和為貴」的「無道」,再連結上信長帶給明智光秀的「不安」,終於把這位古典和文化教養豐富的斯文武將逼上了謀反之路」呢?
筆者的前作《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中引用當時人的光秀評價,證明光秀的確是極富教養的人物,但同時這卻不代表他因此便是以和為貴的「斯文武將」,強調決策要合議的人。
最簡單的證據便是光秀在攻打比叡山不遺餘力,而當他向信長謀反時也沒有多少人知道,看不到他有跟他人合議。當然,因為是謀反,多一個人知道便多一分風險,也有不能商議的問題。既然如此,如果因為信長不「以和為貴」,所以光秀用不「以和為貴」的方式=謀反、軍事叛變來解決,是否能證明光秀「以和為貴」呢?筆者對此則有點疑問了。
以上就蔡教授的文章表達一些己見,誠然本能寺之變與織田信長都是吸引不少讀者關心的議題,筆者日前在香港的連場講座中,尤以信長專題最吸引聽眾,人數也最多,多討論才能吸引更多的討論,在此之言,無意冒犯,謹為交流,還望蔡教授海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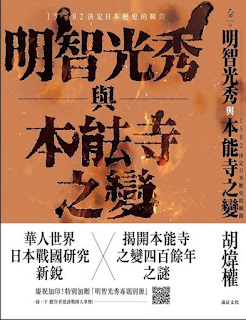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