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責:小編 陳家倫
川越宗一《熱源》第二章〈薩哈林島〉讀後感
帝國之民
第二章故事,來到了遙遠的西方,在1886年11月的北國聖彼得堡的寒冬下,一群信奉社會主義的學生們,不畏帝政的威脅,在寒冬的街頭中公然進行示威,然而他們未經政府許可的示威活動,最終遭到帝國的哥薩克鐵騎驅離。
而在遭驅離的學生中,也包括一位來自維爾諾(維爾紐斯) 具有三重身分的法律系大學生,他既是俄羅斯帝國的臣民,也是出身立陶宛的波蘭人,他就是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Bronisław Piłsudski)。
 |
| 具有俄羅斯帝國臣民、立陶宛出身的波蘭人的三重身分的 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Bronisław Piłsudski) |
與第一章談論落地生根於北海道的樺太阿伊努人不同,第二章將視野轉移到遙遠的西北方,俄羅斯帝國之帝都聖彼得堡。
並以一位身分特殊的人物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為男主角來講述他的故事。做為一位家鄉來自立陶宛的波蘭人,他的祖國波蘭-立陶宛共和國在將近九十年前的三國瓜分波蘭中,遭到俄羅斯、普魯士以及奧地利三國瓜分,消失於地圖之中,成為了地理名詞。
然而波蘭-立陶宛的人們從未放棄過追求獨立的希望,他們投身於軍旅,在拿破崙戰爭中,替法國皇帝拿破崙的霸業貢獻了一份力,因此換取到了華沙大公國的出現,在拿破崙遠征俄國的行動中,波蘭人以最大規模的「外籍兵團」參與戰爭,卻隨者拿破崙的潰敗而瓦解。
華沙大公國的王冠被加戴到俄羅斯沙皇的頭上,然而波蘭人及立陶宛人仍不斷進行反抗,而於1830年及1863年對帝國發起武力抗爭,布羅尼斯瓦夫的父親約瑟夫(Józef)曾經參與1863年的一月起義,追求「共和國」的復興,更於戰火中與髮妻瑪利亞成婚,然而起義遭到帝國軍隊無情鎮壓,因此約瑟夫一度帶者一家避居立陶宛的鄉里,直至此時,兩個兒子早以長大成人,分別於帝都聖彼得堡及烏克蘭求學,身為兩位父親的他也早已忘卻當年的熱血,只求在經商與馬鈴薯堆中找出自己的幸福。
然而這樣的家庭背景,卻使得布羅尼斯瓦夫年輕時被迫搬到鄉下,接觸到了與城市中所見的完全不同的情景,以及接觸到布羅尼斯瓦夫的「母語」,更留下一個仍對波蘭民族及「共和國」偉大復興的弟弟約瑟夫.克萊門斯(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對「祖國」的堅定以及意志。
 |
| 1885年時的畢蘇斯基兄弟合照 中間二人為畢蘇斯基兄弟 左二為哥哥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 左邊數來第三為弟弟約瑟夫‧畢蘇斯基 |
當然相信,對於波蘭歷史有點接觸的朋友,馬上就會想到這位弟弟,就是在未來的20世紀初,帶領波蘭走向獨立,卻也同時是一位追求「波蘭民族與共和國偉大復興」的法西斯獨裁者,更是曾經在波蘇戰爭中,波蘭即將再次在紅軍的「烏拉攻勢」二度滅國時,在約瑟夫.畢蘇斯基領導下於華沙近郊的維斯瓦河擊敗紅軍而創下被稱為「維斯瓦河的奇蹟」的一位波蘭傳奇英雄。
 |
| 約瑟夫.克萊門斯(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 |
但是對於這時候身為一位帝國大學的法律系大學生布羅尼斯瓦夫來說,雖然偶爾會跟同儕開玩笑抱怨,難道我連說自己的母語都不行時,從中略帶無奈的說者自己身為「三重身分」下的帝國臣民的「無奈」
然而比起國家大義或是民族復興,此時布羅尼斯瓦夫更加擔憂的是他在帝都所租的房子中,那位白吃白喝的不速之客的大學學長亞歷山大·伊里奇·烏里揚諾夫(Aleksandr Ilyich Ulyanov)。
 |
| 亞歷山大·伊里奇·烏里揚諾夫(Aleksandr Ilyich Ulyanov) |
眼尖的朋友相信也注意到這位學長也不是位簡單的人物,因為他有一個改變20世紀整個世界歷史動向的弟弟弗拉迪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而這位弟弟我們又稱他為列寧(Lenin)。
這位完全不顧布羅尼斯瓦夫意志而霸佔布羅尼斯瓦夫租屋處的學長烏里揚諾夫,在學校可以說是位風雲人物,充滿文采,但是有時候舉止給人感覺有點輕浮,即使如此布羅尼斯瓦夫並不是打從心裡真的討厭他,這也是為何就算烏里揚諾夫在他家中白吃白喝,布羅尼斯瓦夫也都就這樣算了,甚至還讓學長在自己返鄉回去維爾諾探親時,自封為「舍監」,幫自己看顧聖彼得堡所租的房子。
高牆與幫派
時至1887年,從維爾諾返鄉回到聖彼得堡的租出處的布羅尼斯瓦夫,迎來的是在自己家中喝茶迎接自己歸來的學長,然而這對學長及學弟的孽緣並未因此結束。
布羅尼斯瓦夫也參與烏里揚諾夫與一群用我們的現在口語來說就是「爵卿」們的社會運動的討論會。
在討論未來下一步時,充滿理想的烏里揚諾夫鑑於早前作為社會主義實踐者的前輩們的失敗,認為最大問題在於,帝國的民智未開,如果要翻轉帝國的專制帝政,需要更多的是讓人們進入鄉間的『到民間去』。
而到『到民間去』去運動是最早期發源於俄羅斯的一個具有「民粹派」[1]及「社會主義」性質的活動,有識之士們希望透過深入民間,與農民接觸,在改善農民的生活的同時,也灌輸農民權利等知識,希望透過溫和改革、長期潛移默化的方式,改善最底層的農民生活的同時,也希望透過啟民智改變社會及政治的溫和社會改革形式。
然而在會中的另外一位風雲人物,卻反對這種「沒有成效」的方式,認為當面臨暴政壓迫之時,唯有使用激烈的手法進行對抗,才能使暴政屈服,就在大學的另外一位瘋暈人物綏惠略夫的主導下,充滿激情及熱血,對帝國暴政充滿恨意的大學生們,大都贊同了綏惠略夫激進的武裝派的建議,決定安置炸彈進行恐怖攻擊,以達成他們訴諸自己政治目的訴求。
烏里揚諾夫與布羅尼斯瓦夫雖然反對這樣偏激的政策,更反質問即使偏激的恐怖攻擊真的成功炸死帝國高官,之後又能如何,但在一群以政治為目標從事政治運動的大學生們面前,溫情無法敵過激情,「之後又能如何」,這樣的質問就被淹沒在爵卿們的激情話語中。
布羅尼斯瓦夫遠離了激情的「爵卿」,然而烏里揚諾夫卻出於對同儕的關懷,決意情義相挺為因為哥哥死於西伯利亞的同學坎圖,利用他妙筆生花的文筆,將筆鋒化為刀劍,為「爵卿」寫下象徵他們行動緣由的恐怖攻擊行動的文案,就在這樣的理由下學長烏里揚諾夫儘管反對激進派,而主張到民間去的溫和社會主義,但是仍舊加入激進派的行動。
為了不讓布羅尼斯瓦夫牽連進去,烏里揚諾夫開始刻意疏遠布羅尼斯瓦夫,更要求布羅尼斯瓦夫不要看他所寫的文章,也不要再參加「爵卿」們的集會,以保護布羅尼斯瓦夫不被自己牽連。
然而三月二日的早晨,布羅尼斯瓦夫的住處卻遭秘密警察破門而入。
這時候,他才知道「爵卿」們想暗殺的乃是大人物中的大人物,俄羅斯沙皇。
那麼最終「爵卿」們是否成功暗殺沙皇呢,結果是沒有,他們的計劃提早曝光,只因在計畫即將動手時,其中一位「爵卿」向女友坦白自己與「爵卿」朋友們的暗殺恐攻計畫,寄給女朋友的信最終被俄國警方查到,而當計畫即將動手之時,在「爵卿」們的集會中表現最激進派的綏惠略夫卻突然得了急病,臨陣脫逃前往烏克蘭,群龍無首的爵卿們便在最初反對激進行動的烏里揚諾夫的帶領下展開暗殺沙皇的行動。
布羅尼斯瓦夫雖然明白事態的嚴重性,但他明白自己是清白的,因此儘管面對秘密警察的嚴刑逼供,依舊挺住,然而當他看到在法庭即將宣判之時,那個原本風流倜儻的學長烏里揚諾夫被折磨成不成人形的時候時,仍不免露出驚訝之情。
但是對比人前一條龍,沙皇面前一條蟲,而在法院不斷的對沙皇卑躬屈膝請求饒恕的綏惠略夫,烏里揚諾夫則坦然面對刑責,並盡全力澄清學弟布羅尼斯瓦夫與事件毫無關聯。
看到這邊筆者不經心想,近年來,台港地區從事社會運動及政治運動的學生及年輕人們眾,更可說形成一股風潮,不少人更是在這之中從政,成為社會閃耀的政治份子,然而這些高舉「改革」、疾呼打倒「高牆」的政治「爵卿」們,除了滿腔熱血之外,有多少人是真正考慮到事態的嚴重性呢?
而當你高聲疾呼打倒高牆之時,是否已經想到了未來的高牆的反撲有多高,向你歌頌美好未來的究竟是大聲疾呼勇士出征的「綏惠略夫」,還是堅決反對激進行動,然而臨危受命之下仍義氣相挺志士們恐怖攻擊的「烏里揚諾夫」。
年輕人們對政府、政局的不滿並非壞事,然而當不夠成熟的思緒,遇到煽動者的鼓舞,究竟是建立一個新的「理想國」的石階,還是成為一群「政治新貴」登上大雅之堂下的枯骨。
這也讓筆者想起一部香港黑幫電影「黑社會」,在電影中,飾演黑道人士吉米的古天樂,在老大龍根叔因為幫派內的鬥爭,而一度被囚後,龍根叔曾向吉米說明,自己年輕時便加入幫派,然而最終他還是告誡吉米,如果你要在黑社會生存,就要當最大的頭,不然就趕快遠離他。
然而,從事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的「政黨」及「團體」與「組織」們,又何嘗不是一種型態的「幫派」?
幫派中究竟有多少「綏惠略夫」或者「烏里揚諾夫」,還是企圖為哥報仇的「坎圖」,身在「幫派」或是還未加入「幫派」的你,又是準備如何面對這樣的群體呢?
好了,扯遠了,讓我們回到布羅尼斯瓦夫本人……
審判的結果,不意外的烏里揚諾夫及綏惠略夫等主犯遭處以死刑的極刑,然而更讓他感到心死的是,布羅尼斯瓦夫儘管自認為自己清白,烏里揚諾夫也極力為學弟澄清,但是最終布羅尼斯瓦夫仍被以讓主犯烏里揚諾夫借宿並寫下大逆不道的文章,而被處以流放俄羅斯帝國的國境極東之地薩哈林島,並必須接受懲役15年,他的弟弟約瑟夫儘管人在烏克蘭,跟暗殺沙皇事件毫無關係,也遭到牽連被迫接受流放西伯利亞懲役5年的流刑。
在對現實抱持者絕望的心態下,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便以罪犯的身分,來到了當時俄羅斯人稱為地獄之島的不毛之地-薩哈林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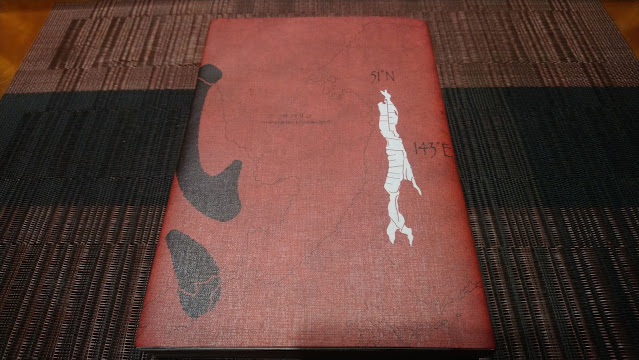 |
| 熱源中文版博客來書鋒 白色部分即是庫頁島(薩哈林島) |
尼夫赫
經過長達兩個月的航行,載運布羅尼斯瓦夫等囚徒的蒸汽船橫越蘇伊士運河,經過印度洋,並在八月抵達薩哈林島,身為囚徒而穿上藍色囚服,並被剃掉半邊頭髮的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Bronisław Piłsudski)就在這背景下,被安排在薩哈林島內陸的村莊魯伊科夫斯科耶(今:基洛夫斯科耶)的木工所,進行肉體勞動。
嚴酷的肉體勞動,以及配給的食糧上之差,加上看守流放囚犯的獄卒對囚犯們的高壓,乃至看者「同伴」不斷在這適者生存的環境中逝去,不斷在精神及心理上煎熬者政治犯布羅尼斯瓦夫,長期的身心折磨,讓他逐漸失去了自己身為「人」的意識。
然而一陣馴鹿的驚恐喧囂聲,以及獵犬獵捕獵物的聲音將已經近乎失去人的靈魂的布羅尼斯瓦夫重新點醒。
在獵犬之後出現的是一位駕者雪橇,彎弓搭箭的獵人,這位獵人,也是布羅尼斯瓦夫在薩哈林島,首次看到監獄看守以及囚徒以外之人。
獵人熟練的取下他的獵物,看了看布羅尼斯瓦夫,便沒再多做表示,而這意料之外之人出現,震撼了布羅尼斯瓦夫,他憑藉者自己對世界及地理的知識問了獵人是不是中國人?
獵人只是靜靜的看者布羅尼斯瓦夫,並簡短的答覆:「尼夫赫!」
簡短的一句話,卻彷彿讓早已失去靈魂的布羅尼斯瓦夫重新找回作為人的「存在」,不久後,布羅尼斯瓦夫從木工所的看守詢問到原來那個獵人可能是薩哈林島的原住民吉里亞克人[2]。
在漫長的牢獄人生中找尋到人生意義的布羅尼斯瓦夫隨即趁者休假日,前往看守所說的不遠處的尼夫赫人的聚落,並表達了想多認識尼夫赫人的想法。
 |
| 尼夫赫人 |
在這個名為「佛斯克沃」的尼夫赫村莊,布羅尼斯瓦夫認識了尼夫赫獵人齊兀路卡,以及他的兒子印丁,雖然齊兀路卡會一些簡單的俄語,但是面對俄羅斯這個龐大的帝國,族人總有力有未逮的憂患意識,也因此齊兀路卡希望布羅尼斯瓦夫這位帝國人教導他不過三歲的兒子學習俄語。
在面對可能的「外邦人」入侵自身的社會中,齊兀路卡或許有了憂患意識,然而他卻不是選擇「野蠻的驕傲」,而是試圖在這「新的時代」進行改變,找出讓族人求生的方式,為此他不惜讓自己可能母語尼夫赫語都還不太熟悉的兒子學會第二語言俄語,為的也是在這「轉變的大時代」中能讓自己的子孫立足於世。
布羅尼斯瓦夫接受齊兀路卡的提案,開始教導印丁及其他尼夫赫人俄語,更不時幫忙尼夫赫人寫一些要給俄國官署的文件,協助尼夫赫人與俄羅斯官僚打交道,在他的幫助下,尼夫赫人得以更容易的與俄國官僚對應,村民們也越來越多人信任這位「外鄉人」,在一次俄羅斯農民企圖強佔尼夫赫人的土地時,儘管文明的農民,以自由民的高姿態看者這些「不懂文明」的「野蠻人」,但是靠者「被文明所拋棄」的罪人布羅尼斯瓦夫,「以文明之道還治文明之身」而戳到農民的痛處,讓試圖強佔土地的農民自知理虧而知難而退。
到了這時,布羅尼斯瓦夫已經不再是所謂的「外鄉人」,而是尼夫赫人的「阿卡恩(大哥)」。
到民間去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Bronisław Piłsudski)已經在被稱為地獄之島的薩哈林島待了數年,他的父親仍不斷的在家鄉奮鬥,向帝國法庭上訴力爭自己兒子清白,以換取減刑,他的那位弟弟約瑟夫.克萊門斯(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 )則是已經結束了長達五年的西伯利亞的流刑,內心則是對於哥哥涉入的暗殺俄國沙皇的行動,惋惜行動失敗以及對哥哥「行動」的勇氣的欽佩,甚至還在寫給哥哥的信中寫到下次也要跟哥哥一起「徹底大幹一番!」的話語。
待在薩哈林島的數年中,布羅尼斯瓦夫憑藉者他受過教育的學識,從粗重的木工工作,轉變到在警察局擔任事務員從事文書工作,每當空閒之時,布羅尼斯瓦夫總是會去尼夫赫人的村莊,既是完成他對於尼夫赫人的研究,也是試圖從折磨身心的流放生活中找到精神慰藉。
就在這樣的日常中,一位奇怪的不速之客卻再次為布羅尼斯瓦夫平穩的生活掀起漣漪。這位奇怪的不速之客名列夫.雅科夫列維奇.史坦伯格(Lev Yakovlevich Sternberg)。
 |
| 列夫.雅科夫列維奇.史坦伯格(Lev Yakovlevich Sternberg) |
史坦伯格是多年前,因為開始走向偏激行動而遭到帝國政府打壓的「民粹派」成員,因為受到激進派的牽連,最終史坦伯格被流放到薩哈林島,但就如同史坦伯格所言,只要他不逃跑,仍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自由行動。
引起這位不速之客來到布羅尼斯瓦夫面前的,則是因為他聽到有一位奇怪的人老是往原住民的吉里亞克人的村子裡跑,而這位老是往吉里亞克人(尼夫赫人)村里跑的怪人,便是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Bronisław Piłsudski)。
史坦伯格訴諸來意,原來俄羅斯帝國的行政機關開始對庫頁島內的原住民在內的異民族感興趣,想要開始研究這些異民族,這些異民族也包括吉里亞克人。
布羅尼斯瓦夫於是也將自己因為興趣使然所寫下的對吉里亞克人的研究交給史坦伯格,史坦伯格看了看之後,覺得驚為天人,並希望布羅尼斯瓦夫可以協助他研究,不但可以協助布羅尼斯瓦夫從俄國本土得到更多需要的書籍,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可能」讓布羅尼斯瓦夫重新獲得自由。
史坦伯格說明如果讓俄羅斯帝國知道自己因為近乎冤罪的審判,讓一位如此優秀的民族學者就這樣埋落在鄉野中,絕對會重新審視布羅尼斯瓦夫的罪刑。
尤其在當時的19世紀末,西方帝國主義盛行,洋槍洋砲憑者船堅炮利,於亞非各地橫行無阻,更敲打許多東方古老帝國的門戶,達爾文生物學上的演化論,更被氾濫的用於社會學及人類學上,成為強調人類、民族及國家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這背景下俄羅斯帝國也對於研究這些帝國境內的異民族,並從中找出符合「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研究觀點感興趣。
然而史坦伯格所要找的,並不只是這類為俄羅斯帝國管制「落後的野蠻人」合理性的同志,他要找的更是那堅持「到民間去」,透過深入民間改革農民生活,啟迪民智完成社會主義改革的「民粹派」同志。
這到「到民間去」的同志,史坦伯格看上了將「到民間去」運動實踐與吉里亞克人站在一起,協助他們與文明打交道,對抗「文明的野蠻」的同為「帝國罪民」的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Bronisław Piłsudski)。
在這背景下,布羅尼斯瓦夫也開始協助史坦伯格研究吉里亞克人在內的庫頁島地區的原住民,進行研究並不時寫下相關的論文。
然而就在這麼一天,文明再次的襲擊「尼夫赫人」,更糟的是,自詡為文明的俄國農民,利用尼夫赫人不懂俄文以及「文明」的運作規則,使得尼夫赫人簽了不知道內容的「法律」文件,最終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透過俄國「法律」出賣了自身的土地給予了「外邦人」。
面對文明如此的「不講理」,身為尼夫赫村人的「阿卡恩(大哥)」的布羅尼斯瓦夫本想據以力爭,為尼夫赫兄弟們奮戰到底,他為尼夫赫人奮戰之心,讓尼夫赫人們都感受到他的真誠,然而這時候,齊兀路卡卻把手放在布羅尼斯瓦夫的肩上,沮喪地跟他說
「算了,大哥,上游還有一片和村子差不多大小的草原,草割一割就能住了。」
面對「文明的野蠻」,尼夫赫人退縮了,或許是明白在龐大的文明面前,自己與族人的挺身反抗有如以軟擊石,然而尼夫赫人的退縮,卻只是更加壓縮自身的生存空間,使之走向更為貧困的慘況,並無限螺旋下去。
布羅尼斯瓦夫看到此處非常心痛,更感到自己的無力以及無能,然而筆者覺得,或許在此時,另一個讓布羅尼斯瓦夫心痛的是,作為一位信奉「到民間去」的溫和社會主義者,希望透過啟迪民智改善社會低下階層的人生活,來達改革目的的社會主義者,最終不但無力於推行「到民間去」,更必須眼睜睜的看者自己的同伴尼夫赫人在「文明」的欺壓下走向衰弱,而真正欺壓他們的,並不是俄羅斯的「高牆」或是「國家」,而是在「高牆」及「國家」下,同樣被壓迫的「文明」的農民,這群本來是布羅尼斯瓦夫最初期望訴諸改革而力行「到民間去」的對象。
「文明」與「野蠻」
在尼夫赫人的村莊遭到「文明」的「外邦人」以「合法」的方式佔據之後,列夫.雅科夫列維奇.史坦伯格(Lev Yakovlevich Sternberg)再次向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Bronisław
Piłsudski)提起俄羅斯帝國的重要學術團體,國立俄羅斯地理學協會開始關注薩哈林島,更希望了解當地的原住民,因此希望布羅尼斯瓦夫能夠協助收集吉里亞克人(尼夫赫人)的一些生活用品。
布羅尼斯瓦夫抱持者虧欠之意下前去尼夫赫人的新村,並跟獵人齊兀路卡說明希望購買尼夫赫人的器物。
在當時布羅尼斯瓦夫的心中,既是對不能保護尼夫赫人的村莊感到愧疚,更也懷疑自己用金錢購買尼夫赫人的器物,將之展示在大雅之堂的玻璃櫃中是否是正確的。
然而齊兀路卡卻開心的接受提案,因為尼夫赫人需要金錢,尤其是當「文明開化來襲」,尼夫赫人必須適應所謂的「文明」之時,這既救贖布羅尼斯瓦夫的精神,也讓布羅尼斯瓦夫下定決心,不再當個旁觀者。
布羅尼斯瓦夫明白尼夫赫人之所以會落得此下場,是因為不懂俄文,簽署了不知出賣自己的文件,那麼他能做的,便是辦學校,讓更多的尼夫赫人接受教育,透過教育得到新知,並足以在「文明社會」中保護自己,以及思考如何做出正確的決定,甚麼樣的文明是尼夫赫人要的,甚麼樣文明是尼夫赫人的不要的,讓這樣的選擇權由尼夫赫人自己選擇。
即使大人可能忙於生活無法來,至少也希望可以讓孩子來,將希望散播在尼夫赫人的下一代。
於是這一次,布羅尼斯瓦夫不再是旁觀者,決定介入尼夫赫的群體中,與它們並肩作戰,面對文明的來襲。
這段期間,布羅尼斯瓦夫協助史坦伯格收集尼夫赫人的文物,甚至當薩哈林博物館成立之時,多數文物都是由布羅尼斯瓦夫及史坦伯格所收集,也因此布羅尼斯瓦夫受到了史坦伯格已經是協會成員的國立俄羅斯地理學協會關注,甚至布羅尼斯瓦夫也寫下並發表了關於薩哈林島上的尼夫赫人的論文,此時的布羅尼斯瓦夫既是尼夫赫人面對文明開化的學校教師,也是位研究人類及民族的民族學者。
隨者父親不斷的向帝國遞請減刑申請,以及遇到新沙皇加冕,布羅尼斯瓦夫獲得特赦刑期減為十年,儘管還必須在薩哈林島待上十年的流刑開拓役,理論上還不能離開薩哈林島。
但是布羅尼斯瓦夫在民族學及研究吉里亞克人(尼夫赫人)的學術成就,讓國立俄羅斯地理學協會,這個有許多帝國達官貴人的學術團體開始注視這位本是帝國罪人的的立陶宛出身的波蘭人。
1899年3月,布羅尼斯瓦夫與他的學生印丁搭上前往帝國的東方邊境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蒸汽船。
此時的布羅尼斯瓦夫是受到國立俄羅斯地理學協會邀請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博物館擔任同館的資料管理人,此既是對於布羅尼斯瓦夫在學術研究上的肯定,更是讓流放十多年的布羅尼斯瓦夫終於離開了流放之地薩哈林島。
多年前史坦伯格與布羅尼斯瓦夫所言的「這些研究『可能』讓布羅尼斯瓦夫重新獲得自由」近乎成真。
印丁做為布羅尼斯瓦夫在尼夫赫村莊中最優秀的學生,也是得力的助教,為了讓印丁有機會受到更好的教育,於是在得到齊兀路卡同意下帶者印丁出島接受更高等的教育。
來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後,布羅尼斯瓦夫得到了向看中他的國立俄羅斯地理學協會進行學術發表會發表研究對吉里亞克人的學術研究。
在發表會中反應熱烈,氣氛良好,然而當最後一位提問者發言時
「薩哈林島異族人的理性對於我國的文明和知識能理解到甚麼程度呢?
從您的演講聽來,雖然有一部份異族人積極地吸收新知,但他們精神文化的發展似乎還停留在原始的巫術階段,所以文明程度發達的俄羅斯人有義務適切地統治他們,帶領他們走向更高的發展階段,這時應該注意的是人種上的特徵,異族人的理性是否具有和我們相同的合理性,能否做到科學性的思考?」
對於這位發問的提問者來說,他只是把他認為理所當然的疑問提出,然而這時候,布羅尼斯瓦夫想起了薩哈林島的尼夫赫人,也想起了不再是國家,而是地理名詞的家鄉,他……做出了回應。
看到這邊筆者認為第二章的部分,比起第一章樺太阿伊努章主要強調的部分在於面對「新時代以及新環境的衝擊」,所做出的「抉擇」及「適應」。
第二章藉由主角布羅尼斯瓦夫特殊的「三重身分」來進行切入,我們會發現在第二章中,面對新環境的出現,尼夫赫人所展現的也絕非「野蠻的驕傲」,而是與第一章的亞尤馬涅克夫(山邊安之助)相同,企圖從中進行「適應」,最終目標也是為了在這「新時代的衝擊中」求生。
而布羅尼斯瓦夫所做的,也有如第一章的阿伊努學校,希望透過教育,讓尼夫赫人也能適應文明,以及從中自保。
換言之,我們可以發現在這段過程中,為了讓尼夫赫人在這段過往未遇過的千古之變及外鄉人的進逼下,「處變不驚,努力求變,適者生存」便是當中想傳達的意思。
而在當時19世紀末,西方國家雄飛,並於東方及非洲各地橫行霸道,然而達爾文的生物學理論的濫觴,社會達爾文主義,卻給了西方國家一個很好的理由,正因為人種有差別優劣,劣等者終將淘汰,適者終將生存,因此在「世界」這個大生態圈中,適者生存下的優秀的文明及民族,將有資格帶領世界,統治其他民族,而對於其他民族也可以透過教育等的形式,讓它們適應「優質的文明」。
為了證明這一點,從民族學中證明一些弱勢的民族不如歐洲國家優秀便是一個方式,因為這些異民族本身落後劣種,因此必須被歐洲人統治,更是當時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的歐洲知識份子的普世價值。
即使是在東方,當原本被視為蠻夷的日本人,面對西方的文明開化衝擊時,也無法抵擋這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的說法,知識分子普遍存在這樣的意識,當中一個案例,便是我們專欄近日曾經介紹的福澤諭吉,基於本來日本便有的神國日本的具有天選色彩的神國意識,結合西方衝擊下,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帶來的衝擊,我們可以看到福澤諭吉無論是在香港,或是在對亞洲一樣遭到西方列強打壓的東方「亞洲同胞」,盡顯對「種族優越感」的推崇。
對於當時的西方知識份子來說,在他們不容置疑的理念中,正因為自身是優秀的民族,因此脫穎而出,並有合理性可以統治世界。而對於曾經被視為野蠻之一的日本人來說,不是反駁這種種族優越論及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是「打不贏,便加入他!」,更期待有朝一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讓日本人有朝一日能成為世界這個生態圈下,適者生存的強者,並壓制亞洲人及英國等西方人。
(有關於福澤諭吉的種族優越感的問題可參考小編松 文章
【福澤諭吉系列(一) 福澤諭吉與香港】
https://sengokujapan.blogspot.com/2021/07/blog-post_07.html
)
筆者覺得我們在第二章中,可以看到作者將主角布羅尼斯瓦夫刻劃成一位帶有溫和社會主義氣息的一位人物,面對文明衝擊所謂的野蠻,布羅尼斯瓦夫決定挺身而出,讓所謂的野蠻做出反抗,於文明與野蠻交錯下,找出中庸調和之道。
而尼夫赫人齊兀路卡為了從大環境的轉變中,找尋族人求生之道,也致力於進行轉變,甚至不惜主動讓自己的下一代學習「外鄉人」的文化及語言。
冥冥之中,布羅尼斯瓦夫與尼夫赫獵人齊兀路卡的舉動也與社會達爾文主義中的適者生存的理念不謀而合,乃符合當時歐洲主流思潮的「落後的文明」需學習「先進的文明」的文化,以達成適者生存的目的。
然而當一位抱持者這樣當時普世價值的知識分子赤裸裸的將社會達爾文主義中的「種族優越感」攤在布羅尼斯瓦夫面前時,他最終做出了省思,並決定向這當時流行於東西方的世界潮流進行反抗。
講到這邊,不知不覺也即將進入到第三章〈錄下來的東西〉,在第三章中,時間將進入20世紀,並回到了故事的原點-樺太阿伊努人,同時也將是第一及第二章的主角們的群星相聚的一篇。
至於筆者何時會在寫第三章的心得呢?相信應該至少會早於庫拉皮卡下船之前吧(喂!)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